股票杠杆网站开户 访乐府学会会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赵敏俐先生(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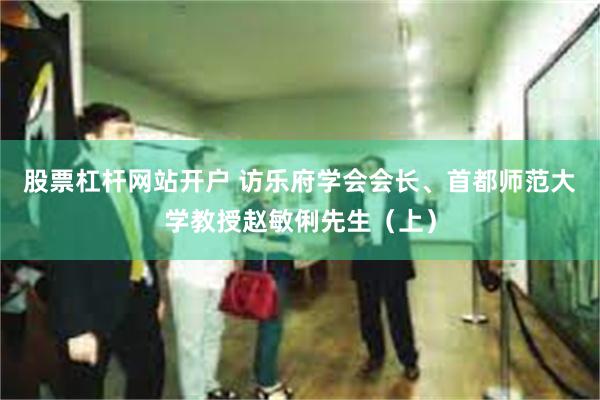
三月初春,中华吟诵广东中心秘书长、广东吟诵团常务副团长刘序老师赴京采访了乐府学会会长、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燕京人文讲席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赵敏俐先生。赵敏俐先生还兼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中国文学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等职务,曾任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20年。
赵敏俐先生1988年春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文学史家杨公骥教授,主要科研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中国古代诗歌、中国现代学术史。出版学术专著有《两汉诗歌研究》、《汉代诗歌史论》、《周汉诗歌综论》、《文学传统与中国文化》、《先秦君子风范》、《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古典文学的现代阐释与研究方法》、《诗经十五讲》、主编《中国诗歌通史》,与人合著《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先秦大文学史》、《两汉大文学史》等著作三十余部,并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二百余篇。先后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成果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等国家和省部级教学与科研成果奖十余项。1993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展开剩余93%赵敏俐先生主持并完成了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吟诵的抢救、整理与研究”(项目号:10&ZD107),出版了《中华吟诵的抢救整理与研究结项报告》、《中华吟诵田野调查研究》(21卷)、这是学界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的有关中华吟诵的抢救整理工作,也是迄今为止对中华吟诵所作的最全面的调查和研究,对吟诵的研究和传承,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以下为访谈实录:
刘序:赵老师新年好!非常荣幸您能接受我们正音公众号本期名家专访。您是中国乐府学会会长,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在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上有非常深厚的学术造诣。今天专程来拜访您,请教您一些专业性问题。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2010年您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吟诵的抢救、整理与研究”的重要成果——《中华吟诵田野调查研究》这一套书,它成书的历程和所具有的意义。
赵敏俐先生:“中华吟诵的抢救、整理和研究”是我们2010年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们之所以要申请这样一个重大项目,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古诗文的创作与欣赏离不开声音,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声音在文化传承中的重大意义。吟诵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基本方式。我们知道,人类在没有文字之前,我们所有的知识传承都是靠口头的。有了文字之后,也只是用于一般的保存和阅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流和文化传承,主要还是要通过口头语言。文字也是在口头语言基础上生成的,文字的阅读和传承也离不开口语,二者相辅相成,所以在人类的文字与语言传承中自然就形成了一些口头的表达方式。这些口头的表达方式有艺术的技巧,在中国文化传承当中就特别重要。尤其是中国古代诗歌,它最初本是口头的创作,是声音的艺术,然后才用文字记录下来,所在它特别讲究节奏韵律之美。你想一想,诗的节奏韵律,如果不用声音来表现,它还有意义吗?久而久之,我们在诗歌的创作和欣赏过程中就形成了一定的声音表达技巧,这就是吟诵。所以说诗首先就是要吟诵的,从先秦开始一直到现代都是这样的。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刊物《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我们要欣赏一首好诗,不懂它的声音之美是不行的,声情并茂地吟诵和我们自己在案头上的默读也是大不一样的。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各种诗体的形成,都要遵从语言的规律,首先要体现为声音的美,并形成相关的诗体与诗格。最典型的是古代的格律诗,它要严格讲究平仄格律。你说“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这样的格律,如果不通过声音来表现,它还有存在的意义吗?所以古人讲吟诗作赋,总是把声音之美的追求放在第一位,总是先吟后写,特别重视吟诵,所谓“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一直到近代的学者鲁迅,他在诗中还说“吟罢低眉无写处,夜光如水照缁衣”,对不对?我们之所以要抢救研究吟诵,首先是因为声音的传承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古诗文的创作和欣赏都离开不吟诵,它有重大的文学价值,音乐学价值和语言学价值。
赵敏俐教授(左)和乐府学会吟诵研究会理事长冷卫国教授(右)在2023年中华吟诵大会上合影
赵敏俐教授(中)和乐府学会吟诵研究会副理事长章剑清先生(左四)、副理事长李志华先生(右四)等参会代表在2023年中华吟诵大会上合影
第二是吟诵的教育学的价值。吟诵为什么有重大的教育学价值?因为它是利用声音来进行教育的重要方式。从小学生接受知识的角度来讲,我们总是要尽量调动人的各种技能,眼耳口鼻舌都要用到。这其中听觉的教育对于儿童的教育来说特别重要。儿童对声音的特殊的敏感,声音的传导可以更为直接地把知识输送到大脑,让儿童更快地接受并成为长久的记忆。我们在全国各地进行吟诵采录的时候,老先生们总是说,他们小时候学过的好多知识都忘记了,但是通过吟诵记下来的古诗文却一生不忘。为什么古人都特别强调读书的时候要背诵,其道理就在这里。
我们一想到自己少年时代的学习生活,总会首先想到琅琅的读书声。特别是在汉语的识字教育和知识教育的早期阶段,吟诵特别重要。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古代最为流行的识字课本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等,都采用了韵文形式,就是为了便于通过吟诵来记忆。儿童读书和学习首先要背诵,通过背诵,你才能记下来。记下来之后才能变成你的知识,在一个人长久的一生中,你可以不断地咀嚼,不断地回味,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加强对知识的理解。所以我们说吟诵的教育学价值巨大。我们现在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在这个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这就等于在小学教育中,浪费了儿童学习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听觉器官的功能。当然,声音的教育并不仅仅是古诗文的吟诵,也包括现在的朗诵,还有与之紧密相关的音乐教育,但吟诵在当代中小学教育中的缺失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些年我们坚持在全国中小学语文教学中推广吟诵而深受欢迎,其道理也在这里。所以我们说吟诵的教育学价值巨大,值得当下的教育专家进行深入的研讨。这也是我们要抢救它的一个重要原因。
原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吟诵分会秘书长,首都师范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徐健顺先生采录姚奠中先生
但是吟诵的价值这么重大,可是过去却没有人做过系统的研究工作。在过去旧的教育体系下,吟诵都是代代相传,人们习以为常,不做专门的研究。到了近代,在反对传统文化的时代潮流下,我们把中国的传统教育模式废弃了,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模式。这样就使中国传统的吟诵中断了,当代中国会吟诵的人已经很少了。如果想把这些吟诵搜集保存起来,就应该尽快地组织全国的人力进行抢救性采录。所以我们申报的这个重大项目题目就叫“中华吟诵的抢救、整理与研究”。我们首先强调的是抢救。其实我们下手已经太晚了,我们这个课题立项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项目从2010年12月立项到2018年结项,我们在全国费尽了力气才找到并采录了一千多位老先生。我们采录的主要对象都是七十岁、八十岁以上的人。到现在,我们采录过的这些老先生,已经有一半以上的都不在人世了,所以我们说是抢救。
吕君忾先生参加2009年首届中华吟诵周开幕式
刘序:像原中华吟诵学会副会长、广州诗社副社长、诗词名家、分春馆掌门、粤语吟诵承传人吕君忾先生,他是我的老师,现也已离开了。
赵敏俐先生:对啊,吕君忾老师还不是这里年龄大的,我们采录周有光老先生的时候他已经105岁,我们采录过姚奠中、霍松林、文怀沙、南怀瑾等一批老先生,采录他们时候都是九十多岁,一百岁左右。你们想想,即便是这样的人,他们从小接受的主要也不是传统的私塾教育了。他们的吟诵大都是从他们的老师辈儿或者他们的亲属(如父母、姑姑舅舅等等)那里传承下来的。所以我们这个采录工程,“抢救”的意义是重大的。
我们把采录的成果分成三种书出版,第一是《中华吟诵的田野调查研究(21卷)》。这个是我们采录的老先生们的讲话录音,是他们的口述史,主要讲他们如何学习吟诵,学习吟诵的经验体会,他们对吟诵的认识等等。第二是我们依据整个采录过程所总结的研究成果,出了一本结项报告。这个结项报告详细地介绍了我们吟诵采录项目的缘起,各地吟诵现状的分析,名家谈吟诵的认识,并且对吟诵抢救的意义和它的当代传承等问题进行了理论的思考与总结。结项报告全方位地记录了我们这次的重大项目的整个过程和我们的收获。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采录下来的老先生们的吟诵,和他们的珍贵影像。我们已经交给了现代出版社,申报了国家出版基金。原计划是2024年要出版的,现在还没有印出来,但是2025年也很快会出版的。
刘序:出版的形式是?
赵敏俐先生:音像出版。我们要出一个u盘,包括老先生吟诵的录音和录像,我们对每一首吟诵都做了分析。把这三套书合在一起,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全部的成果。要对吟诵进行全面研究,最好把我们这三项成果结合一起来看。
2010年采录“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
刘序:您能介绍下这个项目的团队情况吗?
赵敏俐先生:我是这个项目的首席专家,主要负责人还有徐健顺教授和朱立侠博士,以他们为代表组成一个采录团队。团队成员来自全国各地,以首师大为主。我们成立了吟诵采录工作组,负责人是我,队长有徐健顺、朱立侠等六人,核心组主要成员有12人,主要参与者有38人。项目完成后,我们在整理成果的过程中又成立了中华吟诵田野调查研究编委会,主编是我,副主编是徐健顺、朱立侠,编委有20人。编辑整理人员有109人。另外呢还有很多人帮助过我们。在这个项目的采录过程当中,我们到每一个地方去都得到了当地好多的人热情接待和支持帮助。
刘序:这么巨大的工作量,项目经费足够吗?
赵敏俐先生:因为这个项目比较重要,国家社科基金给我们提供了三次支持的经费。第一次是重大项目的下达经费八十万,第二次又滚动支持我们八十万,第三次又支持了六十万,加在一起是二百二十万,但是这个钱也远远不够。我们到全国各地去采录,分成好多小组,以年轻人为主,他们到各地去采录,都是最简易的住宿条件,吃得非常简单,非常辛苦。我们去采录的这些老先生,年龄都很大了。去采录他们时,想要给老先生带一点礼品,但是项目经费里没有这项开支,也没有办法报销。采录小组往往就自费买几只花啊,买点水果啊,或者小礼品啊送给老先生,表示对他们的尊重。除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经费之外,我们向学校和相关部门还申报了财政项目,他们也给了我们一些支持,这样我们才能把这个项目做下来,要不然是做不下来的。
2008年采录周笃文先生
刘序:这么浩大的工程,全国各地光是差旅费都不少。
赵敏俐先生:我们走遍了全国各地,除了西藏没去,其他省份都去了,包括香港澳门台湾。我们还到日本和韩国做了采录,在成果里面都有介绍。
刘序:参与项目有不少人,他们平时工作学习不受影响吗?
赵敏俐先生:我们要把很多的精力都投入到这上面。有很多人都是自愿参加。主要负责人,像徐健顺老师,他这些年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到这个项目上,最终把身体都熬垮了。他现在生病还没有完全康复。因为他是全力的投入,所以把身体累垮了。我们做这个项目花费了巨大的精力,采录来的东西,光是口述吟诵材料就有二十一卷,把这些东西都整理出文字,你想想得下多大功夫。这个整理还相对容易一些呢,更难的是我们采录来的这些吟诵的音像资料,我们也要进行整理和分析,更不容易,要重新做很细致的工作。在出版的时候我们还要征求采录者的意见,得到他们的授权。如果他本人去世的话,还要征求他的亲属的意见。因为关涉到著作权保护,他们不同意的话,我们就不能出版。我们出版的都是经过他们授权的。我们要一个人一个人地签授权协议,光这件事我们就得下很大的功夫。
南开大学“中华吟诵的抢救、整理与研究”课题组组长叶嘉莹先生
(《光明日报》 2013年05月28日15版)
刘序:这项工作确实很复杂,很艰难,我想你们这些工作是可以写进吟诵研究史的。
赵敏俐先生:我们采录的这些东西特别珍贵。有许多老先生,他的一生就沉浸于吟诵里,可能只留下一个吟诵的调子。假如你对吟诵不感兴趣,你听一听这些吟诵,好像也没有什么,也许你还会觉得也不太好听。也许你就会想,花这么大的人力和财力采录这些东西值得吗?我们觉得是特别值得的,每一个吟诵调整都很宝贵,是活态的声音,是历史的记录,是这些吟诵传人亲自传承下来的宝贵文献。过了多少年之后,它们的价值就更加珍贵了。
陈以鸿先生吟诵采录
刘序:我去年采访刘德隆先生,他就说日本人曾经去陈以鸿先生那采录过他的唐调。
赵敏俐先生:对的。有些老先生,他们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到上面。你看叶嘉莹先生,晚年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差不多都用到吟诵的传承和推广方面。我们过去对叶嘉莹先生也不熟悉,我们去采录她,说明了我们的目的,她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采录。她前后用了八个半天的时间,向我们非常详细的介绍了她对吟诵的认识和体会。叶先生的事迹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部《中华吟诵田野调查研究》第一卷,首先介绍的就是对叶先生的采录,一共用了九十二页的篇幅,把对她的采录全部记录整理下来。
2009年采录叶嘉莹先生吟诵录音
刘序:这个最好是配合那个u盘音频来看,对吧?
赵敏俐先生:对。看她的音频,然后再看她这些东西,就能对她的吟诵有更多的了解。
刘序:叶先生的调是跟谁学的?
赵敏俐先生:其实叶嘉莹先生的吟诵,主要是从她的亲属那里传下来的。她是满族人,但是满族人那个时候读书都汉化了,她们说的就是传统的北方话。她的吟诵有家学的一些渊源,再就是她的理解。因为有了基本的家族传承,掌握了相应的语言学的知识,再加上她自己对古诗文的深入理解,叶先生对吟诵有特别深的体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吟诵风格,并且有对吟诵的深入研究,所以她自然就成为当代吟诵传人当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吟诵好听不好听,有几个很重要的关键。首先是发出的声音要字正腔圆,字正腔圆才能美听,意义的表达也会非常清楚,这是声音或者音乐的基础。第二个就是语言的基础。汉语是声调语言,有平上去入四声,你要掌握四声的发声技巧,要符合汉语发声的基本规律。四声又可分成平声字和仄声字。首先说平声字,因为它的声音是平的,可以发出一个很长的音。比如我们说“阿”,可以把声音拖的很长。但是仄声字却不能,它的声调有高低变化,你就不可能发出长音。比如我说“去”,你怎么能把它读成长声啊,是不可能的。它的发声从高到低,时间一长,你就发不声来,没有气儿了。
刘序:再读下去就变平声调了。
赵敏俐先生:对啊,那就不行了吧,所以说吟诵的基本原则一定是平长仄短。因为是平声,它可以发的音很长,而仄声自然就短。又因为平声可以发出长音,就不可能在很高的声调上一直保持下去,往往声调就低一些。因为仄声短,为了突出仄声的意义,它的声调自然就要高一些。所以说吟诵里边语言的规律,第一是平长仄短,因为汉字的四声就应该这样发声。但是平低仄高则不一定,有些地方就是平高仄低。所以这一点并不是绝对的。
刘序:粤方言阴声调就相对高一点,阴平最高(阴入同),然后是阴上、阴去(中入同),再到阳上、阳去(阳入同)、阳平。
赵敏俐先生:对,普通话现在也是平声高嘛。但是这个呢只是在平常说话的情况下是如此,吟诵的时候呢,还需要做特殊的处理。它的长短和高低都是相对的。第三个重要的因素呢,就是你对作品的理解。一首诗,它表达的是一种悲伤的情绪。你如果用欢快的语调去吟诵,那显然不行的,对不对?一首诗的的情感表达,也会有高低起伏的变化。所以对作品的理解很重要。好的吟诵这几个方面都要把握到位。
刘序:所以必须要依字行腔,依义行调。
赵敏俐先生:对,为什么老先生的一些吟诵特别珍贵呢,都是他们一生对那个吟诵的总结,包括发声的技巧,对平仄高低的掌握和对作品的理解,是他们长期实践的结果,有独特的风格,所以才特别珍贵。
刘序:2018年您主编了吟诵研究资料汇编古代卷和现代卷,由中华书局出版。能否就这套书简单介绍一下编写初衷、内容特色和学术价值?
赵敏俐先生:吟诵是中国古代的传统的读书方式、创作方式和传承方式。我们中国古代人就把它看成是日常生活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人在古代做过专门的系统的研究。对吟诵进行系统的研究,其实是到了近代以后。因为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被破坏了,这时候呢人们才想到古代吟诵的价值,有些人才开始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于是我们想要考察,这个吟诵的根基到底在哪里?古人有没有相关的论述?即便没有系统的研究,也应该有一些相关的论述吧。所以呢我们就想把这些材料搜集起来,为今后的吟诵研究提供一些历史的支持。看古人在他们的只言片语当中,在他们的日常的著作当中留下了哪些关于吟诵的论述。这些论述呢,有的时候虽然很简短,但是价值非常重要。
刘序:这些论述在哪些经典有所提及?
赵敏俐先生:中国传统的经典著作当中都有,比较零散。
刘序:那等于要翻阅大量的文献资料。
赵敏俐先生:是的,要翻阅大量的书。相对来说呢,在古代的诗歌的传承和评价的理解方面记录的东西多一些,还有一些人吟诵的理解比较深,他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像朱熹,王阳明,他们都有一些相关的论述。我们要对吟诵进行研究,首先要了解历史。要了解历史,我们就首先要找材料。所以我们才做了这样的一项工作。
刘序:王阳明在越地讲学期间作了多首咏良知的诗歌,和同时期广东增城另一位思想家学问家湛若水先生的交情很是深厚。
赵敏俐先生:对,作为一个思想家啊,他讲知行合一,特别强调读书的重要性,他就发现读书法非常重要,所以他在中国古代差不多是关于吟诵论述最多的人。
刘序:现代卷的内容有什么特点和价值呢?
赵敏俐先生:五四以后西学兴起,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也引发了人们的思考,这时候有很多老先生们开始关注吟诵,研究吟诵,留下了最早的第一批资料。有很多人关于吟诵的论述也特别珍贵。像唐文治、钱基博、朱自清、叶圣陶、赵元任、朱光潜、夏丏尊、杨荫浏、任半塘、俞平伯等人,有很多关于吟诵的精彩论述。所以现代卷里边的内容更丰富,材料很多。我们在那里边还介绍了1946年,魏建功先生代表国语推行委员会邀请黎锦熙、朱光潜、冯至、朱自清等22位著名学者在北大开会研讨诵读方法一件事,留下了《中国语文诵读方法座谈会记录》,发表于《国文月刊》1947年第53期。
刘序:您的研究领域很广,学术界对您在艺术生产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歌诗这方面有很高的评价,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您是第一作者。可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艺术生产史。艺术生产史包括了几个层面维度,以及艺术生产史和艺术史、美学史、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之间有什么关联?
赵敏俐先生:我研究这个艺术生产史,首先是和我做的研究对象有关系。我当时的主要研究是中国古代的歌诗。
刘序:为什么是歌诗,不是诗歌?
赵敏俐先生:因为中国古代的诗在最早的时候都是可以唱的,本来诗就是歌,歌就是诗。诗与歌后来分家了,二者就有了不同。所以诗歌这个概念,在中国古代就包含诗与歌两种形态,就是诗与歌的相加。但是在我们现代人的观念当中,说到中国古代诗歌,一般人都把它理解为用文字写成的诗,重点在“诗”上,一般人并不特别关注“歌”的意义。
刘序:朗诵的诗?
赵敏俐先生:对,在我们的观念当中,使用诗歌这一概念,一般人都把重点放在“诗”上,专指用文字书写下来的诗,或者用朗读的方式传承下来的诗,而把“歌”字忽略了。我现在要重点研究那些可以歌唱的诗,没有办法,只好把这两个字调换一下位置,由诗歌变成歌诗,用它来专指那些可以歌唱的诗。
刘序:在古代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称谓?
赵敏俐先生:歌诗这个概念不是我自己的创造。在汉代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里,就把中国古代的那个诗歌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只用来诵读的诗,在汉代把这样的诗都称之为“赋”,一种是可以唱的诗,就叫“歌诗”。
刘序:就是“不歌而颂谓之赋”。
赵敏俐先生:对啊,不歌而诵的诗,在汉代叫做赋,可以歌唱的叫做歌诗。所以我要把这个中国传统的“歌诗”概念拿出来,专指中国古代的那些可以唱的诗,重新使用古代的这一概念。我为什么要强调歌诗?是因为在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传统里,对诗的理解,重点强调它的思想意义和文字意义。站在这一角度看,一首诗唱和不唱的意义区别不大。这一点在当代教育体系当中表现的特别明显,我们倾向于理解诗歌的思想,老师在中小学给你们上课的时候讲一首诗,他给你们讲怎么唱吗?基本不会。他只讲这首诗表达了什么情感,表达了什么思想。当我们进行思想研究的时候,诗和歌之间也没有多大的区别,对不对?但是我们要从艺术的角度切入,深入研究并分析中国的古代的诗歌,就会发现诗与歌之间有巨大的不同。那些可以唱的诗和文人案头写的诗,在创作的方法,诗歌的功能,在它的表现方式等很多方面,二者都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
那么如何解决这些现象呢?我们过去没有关注。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中,我们总是习惯于阐释诗歌的思想意义。从思想的角度来分析一首诗,无论是可以歌唱的诗和只用于诵读的诗,我们都采用一样的分析法。在古代社会,那叫儒家的诗教。在当代社会呢,我们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分析法。可是我们如果换一种解读诗歌的方式,不是从思想入手而是从表现方式入手股票杠杆网站开户,就会发现二者大不一样。你想一想,一首用于祭祀或者日常娱乐的歌诗,和李白、杜甫、陶渊明等人专门用来抒情写志的诗,创作的出发点一样吗?不一样。表达的方式一样吗?也不一样。它的艺术形态一样吗,也不一样。所以说对于不同的诗歌,我们就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发布于:广东省